 |
 |
今天是星期六,我們之所以知道今天是星期六,是因為昨天是星期五。但我們所謂的「日」(a day)究竟是什麼意思?經常有人說英語是最豐富的語言,字彙不停地增加,所以我們英語系國家讓「日」指涉兩個不一樣的意思──太陽二十四小時自轉一圈,還有夜的反義詞──未免稍嫌荒謬。儘管很顯然會造成溝通上的錯誤,我們仍然堅持這種笨拙又粗野的做法,因為我們死腦筋,而且顯然有一點愚蠢。其他許多語言都不會做這種蠢事。例如荷蘭語就採用兩個不同的字來規避這種混淆(Dag指的是白天,Etmaal指的是二十四小時),而保加利亞人、丹麥人、義大利人、芬蘭人、俄羅斯人和波蘭人都有類似的做法。不過和Etmaal最接近的英文字是Nychthemeron(希臘語的「日與夜」),比較像是芬蘭重金屬樂團的名字,一看就讓人傻眼。我從來沒聽哪個人用這個字來講話,連科學家都假裝根本沒這個字,所以它成了語源學家飼養的一隻營養不良的寵物,碰到特殊場合才從籠子裡拿出來,譏笑它有多麼荒謬。
不過以英語為母語的人照樣這麼混下去,不然就是偶爾改變遊戲規則,用夜晚做為時間的測量單位,就像我們訂旅館房間的時候,狡猾地用fortnight這個盎格魯撒克遜文字來代表連續十四個晚上的意思。但這種做法也不是每次都行得通,因為旅行社的人必然會問:「是十四天十三夜嗎?」然後我們必須像小孩背九九乘法表一樣,用手指頭挨個兒數一遍。但我們不要給與太嚴厲的批判,因為這多少是遺傳性的弱點。到底怎樣才叫做「日」?相關的術語一直有個很讓人傷腦筋的問題。在三世紀,羅馬哲學家森索瑞努斯(Censorinus)主張,二十四小時的週期應該命名為「民用日」(civil day),而白晝應該被稱為「自然日」(naturalday)。儘管看似合理,七世紀一群沒事找事的學究把二十四小時的循環週期改成「自然日」,反而用「人工日」(artificial day)來代表白天,把事情攪和得更加混淆。
但我們不必花心思把定義背下來嚇唬朋友,因為現代天文學又反過來,用「民用日」來描述地球自轉一天的時間。如此一來,原先代表兩種意思的「自然日」,現在已經不再指涉任何意義,而「人工日」現在指的是燈泡發出的光。聽懂了嗎?不,我也不懂……但我擔心本章的內容幾乎沒有簡單的地方,連「日」的起點和終點都很難定義。
|
|
 |
身為懂得禮數的主人,既然晚餐即將開始,我們必須向賓客示意,很有禮貌地請他們從沙發站起來,往餐桌的方向移動。不過因為沒有放名牌,我們發現朋友們猶豫了一會兒,忖度究竟要坐在哪個位子。我們看到那對夫妻很快想了一下,思索究竟應該坐在一起,或是坐在彼此的對面,方便他們藉由同住多年所培養出的默契,用不著開口,直接用細微的眼神或表情溝通。其他人問我們是不是要一男一女比鄰而席,而那位柳腰纖細的素食者看自己比我們其他人都嬌小,很有禮貌地主動表示要坐在比較侷促的角落。
大伙兒一時之間拿不定主意,場面有些傻氣,有人心領神會,不免尷尬地笑了笑,但從這個社交上的尷尬場面,就知道為什麼歷史上大多數的文化都有潛規則,決定哪個的人屁股該擺在哪個座位、哪個人的屁股根本不受歡迎。浦魯塔克在他的著作《論文集》(Symposiacs)當中,思考究竟是主人要負責幫賓客安排座位,還是讓他們自己決定。但實際上羅馬的東道主多半會插手干預,使得宴席的座位安排反映出羅馬的社會階層高低。在這種情況下,大伙兒不會圍著餐桌吃飯,而是各自斜躺在長椅上,主人會坐在首席,身邊是他偏愛的客人,而飢不擇食的食客、令人尷尬的叔伯,以及從事行政工作的悶蛋,被趕到最遠的沙發末端,遠離身分尊貴的客人。
為了更清楚地表明主人家不是很歡迎他們出席,這些身分比較低下的客人的酒食可能都是次一等的。而他們心裡也有數,因為他們會親眼看到美酒佳餚從面前經過,卻怎麼也拿不到,像是在取笑他們一樣。身分低微的人陪同受邀的賓客參加這種晚宴,感覺一定像是在搭乘橫越大西洋的班機時意外闖入頭等艙,迎面看到像樣的葡萄酒杯和美味的餐飲。相較之下,等我們回到自己狹小的座位,把空服員砰一聲丟在折疊桌上,猶如橡膠一般的預熱千層麵放進嘴裡,一定覺得味道和聚乙烯沒什麼兩樣。
希臘男人一起吃飯的地方叫做「男廳」(andron),通常男人會先支開妻子,但就算有夫人坐鎮,他們照樣會邀請高級妓女、舞孃和性感的美女吹笛手來助興、調情,或獻上更明目張膽的抖動式裸體服務。羅馬人似乎不像他們的愛琴海鄰居,妻子往往可以挺直背脊,坐在比較正式的椅子上,而她們的丈夫則斜躺在長椅上。恐怕很少有人邀請尋常人家的女子躺著吃飯。
羅馬的勢利眼把不受歡迎的人趕到宴席外圍,中世紀的英國也大同小異,安排宴席的座位時,主人和那些跟他關係最親近的客人,坐在用底座架高的固定桌(table dormant),位在大廳的盡頭。這是英國婚禮常見的排座法,主人可以居高臨下,凝視縱向排列在他面前的一張張擱板桌的賓客。他歡迎這些人來吃飯,但認為他們「社會地位低下」(below the salt),意思是他們不配坐在勛爵架高的餐桌上。固定桌上擺了美麗的鹽罐(salt cellar),多半是手工製作的銀器,罐子上鑲著閃亮的珠寶,在勛爵的右手邊一閃一閃的。有時鹽罐就像一艘維妙維肖的小船,叫做「船形盆」(nef),到了十六世紀,船形盆甚至有可以運轉的機械零件和小輪子,可以在桌上推來推去,彷彿是專為億萬富翁的稚齡幼兒打造的鍍金玩具垃圾車。
|
|
|
 |
 |
我們身處在行動電話的時代,SIM卡的數量比地球上的人口還多,我們很快就適應了手機不可或缺、便於攜帶的特質,以致於現代的小孩聽到我十幾歲時如何用市話打電話給朋友,還要事先約好碰面的時間與地點,全都驚呆了。這聽起來顯然比較像是黑暗中世紀的古老寓言,而非一九九九年的真實情形。在年輕人的眼中,連接著塑膠線的電話顯得古意盎然,而對我們其他人來說,這是我們住家和辦公室長久存在的科技。但曾經在十九世紀末的某一段時間,電話只是兩位相互較勁的傑出科學家腦子裡的概念而已。
亞歷山大.葛拉漢.貝爾(Alexander Graham Bell)是蘇格蘭出生的一位發明家,由於母親耳聾,因此他畢生鑽研通訊科技,希望能幫助和他母親一樣的人。其後,貝爾遷居到波士頓,並用他們的溝通技術輔助聽障人士,貝爾開始摸索一種全新的裝置:電子說話機。他和才華出眾的電機工程師湯瑪斯.華生(Thomas Watson)合作,他們透過電線傳送音頻的裝置固然前所未有,但並非獨一無二。一八七六年,貝爾提出專利申請時,無意間發現自己和另一個人不相伯仲,對手只比他晚了兩小時。
做為官方認定的勝利者,貝爾幾乎沒時間開香檳慶祝,反而很快打起一大堆侵權官司,每一件案子的被告都想剽竊他的創意。在這六百多件訴訟案當中,最大的一宗案件很快就搬上檯面。在貝爾達成技術突破之後不久,他向美國第一大企業西聯電報公司(Western Union Telegraph Company)兜售這項技術,但西聯不願支付貝爾要求的十萬美元。就像高中足球隊的四分衛對戴眼鏡的女文青總是不假辭色,他們鋒頭太健,不屑和這種小角色成對。不過,就像浪漫喜劇的結局,書呆子貝爾摘下眼鏡,放下頭髮,露出她辣妹的本色──簡而言之,電話在市場上一炮而紅。
西聯對自己的錯誤決定感到悔恨不已,發誓絕對不能被比下去,於是請了當紅發明家愛迪生(Thomas Edison),以及吃了悶虧的復仇者葛雷,試圖迴避著作權法,把貝爾的設計做出適當的更改,這樣一毛錢都不必付給這個蘇格蘭人。貝爾和他的合作伙伴質疑西聯公司侵權,準備提出訴訟,不過讀者恐怕會認為他們一定非常吃虧,因為西聯公司有的是錢,大可聘請美國任何一位律師,砸重金讓律師在華府各級法院表演。然而,就像高中運動健將和女文青的故事,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一八八八年著名的判決,顯示大法官是貝爾隊的支持者。
這個逆轉勝的故事或許可以稱為「大衛決鬥歌利亞」,只不過後來等於是歌利亞不斷用自己的武器打自己的臉,而不是被大衛的小石頭打倒。既然被聯邦最高法院判決敗訴,西聯公司決定和這位新貴妥協:他們交出八十四項個別的專利權,以及在全美五十五個城市安裝的五千六百支電話的所有權,並同意在一八九六年之前不再涉足電話業。如此一來,貝爾有十七年的時間可以自由發展,或者應該說是「自由支配」。基本上,貝爾就像留著一臉大鬍子的諸侯王,得以主宰電話市場。西聯公司的管理階層只專注發展他們的搖錢樹:電報,卻不小心打開籠子的門,把裡面的天生掠食者放出來。這段歷史相當於一家市值數十億英鎊的公司開口說:「新興的行動電話業務都是你的,條件是只要我們可以繼續製造呼叫器就好。」
改變世界的不只是貝爾的天才,或是西聯公司痛擊對手的反射動作。舉個例子,本人幾乎全聾的大發明家愛迪生,對電話的迅速普及至少做了兩大貢獻。一八七八年,他用碳粉發明了超敏感的麥克風,讓電話使用者可以用正常的音量說話,不必吼得臉紅脖子粗。只可惜沒有人把這件事告訴通勤火車上那些吵死人的商人。不過愛迪生的另一項建議就不是在科學裝置上動手腳。只是一個字罷了。
|
|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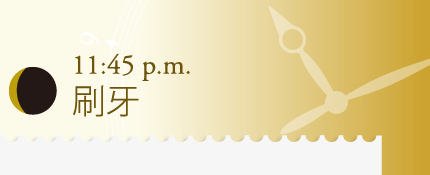 |
當我們愉快地刷牙時,帶有薄荷味的水一點一點往下巴流,我們可能突然發現嘴裡有個疼痛的膿瘡,或者有哪一顆牙齒在搖晃,然後我們第二天早上大概會打電話給牙醫,相信他們牆壁上掛的鑲框證書可以證明他們大概不會害我們受傷。但中世紀的人如果不看牙醫,也可以找另外一種人幫忙,這些人的店面擺著一根柱子,纏著染血被單,窗戶和牆上掛著一個個濺出人血的桶子,和一個擺滿各種恐怖工具的架子。在店面布置這些染血的道具是為了顯現牙醫的經驗豐富,好叫病人放心,雖然看在我們眼裡,只能證明他是個心理變態的瘋子,正在炫耀自己的戰利品。最令人發毛的是,這個準備把鉗子伸進病人嘴裡的傢伙,很可能也是他們的理髮師,因為在拔牙的專業技術方面,懂的人固然不少……但每一個都很恐怖。
其中最不濟的是單純的理髮師,本質上就是兼差拔牙的美髮師。然後是訓練比較精良的理髮手術師(barber-surgeon),他們擁有基本的醫學知識,可以執行最簡單的手術。這兩個相互競爭的階級又受到讀過大學的醫師所鄙視,後者幾乎完全不動手術,主要的興趣是研究醫學理論。數百年來,政府在不同的階段給這幾個不同等級的專業人士設定界限,然而只有醫學受到官方的管制,表示牙痛的病人可以合法地被揮動刀子的理髮師按在地上,如同被擊倒的拳擊手,手腳不停地掙扎,想在裁判數到三之前爬起來。
從這裡不難看出為什麼人人都應該努力避免拔牙手術,並且保持健康的牙齒和牙床。
|
|
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