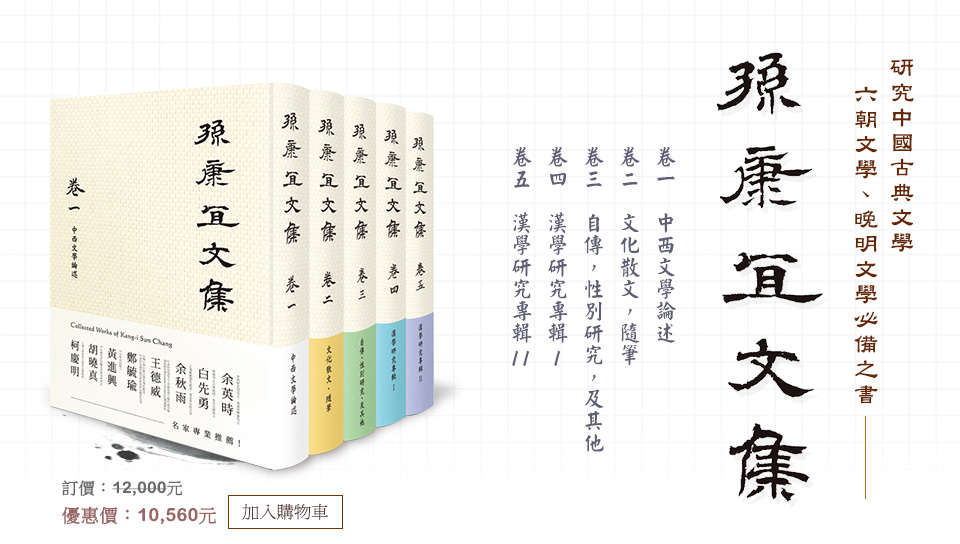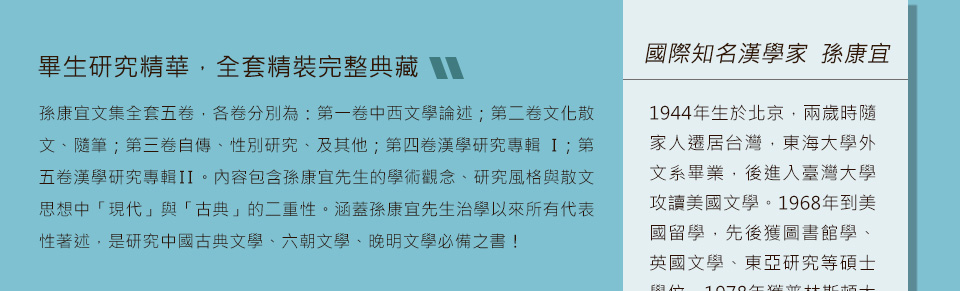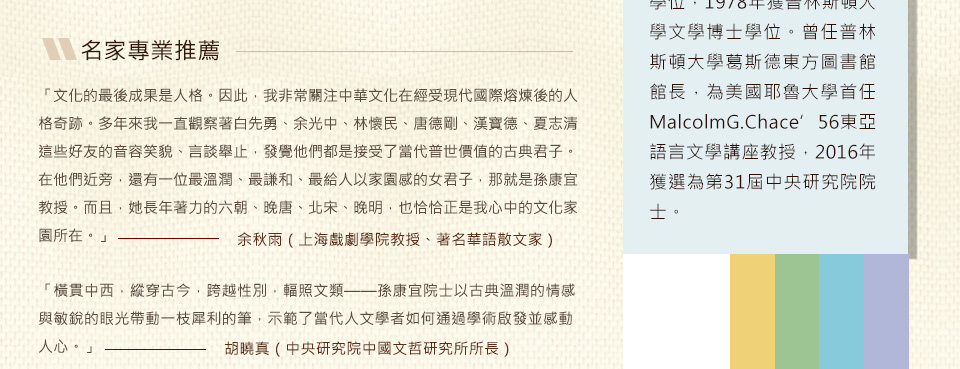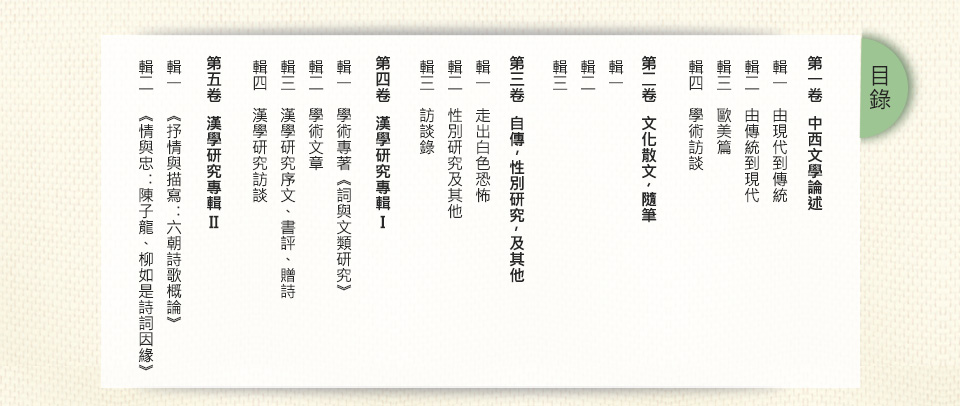【錢謙益及其歷史定位】
歷史上對於錢謙益(一五八二-一六六四年)其人的評價,向來毀譽不一。錢在世的大部分時間裡一直被公推為詩界巨擘、文壇領袖,以他主盟的虞山派在明末的諸多詩歌流派中聲名顯赫,數以百計的弟子向他問學不輟,若不是明朝覆亡,錢肯定會彪炳史冊。然而一六四五年,滿清鐵騎攻陷南明的都城南京,錢的命運也就此急轉直下。是時在福王朝廷就任禮部尚書的錢謙益迅速投降了清人,儘管錢後來對於自己的降清搥胸泣血,深自愧悔,儘管他在一六四六年即致仕歸鄉,中國許多文史學家卻不肯寬恕(或者說忘卻)錢短暫的「叛國投敵」行為。在他們心目中,錢謙益始終是「失節者」的代名詞。
富有諷刺意味的是,第一個以官方形式聲討錢謙益的人正是滿清的乾隆皇帝,他對錢作出的結論是:「大節有虧,實不齒於人類。」到了一七六九年,即錢死後一百多年,乾隆下詔禁毀錢謙益的全部詩文,後來還著意指示「無使稍有存留」。乾隆首先是憎惡錢謙益身事兩姓,有虧臣節,同時又對錢降清後尚在詩文中「陰行詆謗」滿人的行徑怒不可遏。故此,在一七七○年的一首御制詩中,乾隆指斥錢謙益「進退都無據」。
有趣的是,乾隆皇帝褒顯忠貞風勵臣節,詔旌明季死事諸臣為大明英烈。我們由此注意到,即使是在十八世紀七○年代大興文字獄的時候,乾隆也極少公開指責那些在十七世紀為前朝捐軀的忠臣義士。J.D. Schmidt對此解釋得很到位:這是因為清政府「希望當代的官員能夠以同樣的忠誠為本朝效命」。知道了這一背景,便不難理解乾隆為何於一七七六年為明朝忠烈陳子龍(一六○八-一六四七年)平反昭雪,還英雄以本來面目,凜於陳氏的「浩然正氣」,乾隆將其追諡為「忠裕」。
與此相反,對於那些身事明清兩朝的官員,乾隆皇帝決定予以懲戒,至於處分輕重則因人而異。於是,一七七七年乾隆下詔為錢謙益一類的「無行」降臣專門在國史中增立〈貳臣傳〉。在乾隆看來,錢謙益「反側貪鄙」,正是「貳臣」這一類別的不貳人選。一七八一年,乾隆進而將錢謙益及其他幾個「貳臣」貶入〈貳臣傳〉乙編(以示比列入甲編的洪承疇諸人更低一等)。乾隆諭旨說,錢謙益之流歸順本朝不過是「謬託保身」的一時權宜,作為一種懲戒,錢謙益的詩文集被皇皇巨著《四庫全書》澈底擯除在外。
【「二二八」的聯想】
在我們抵達臺灣的第二年(一九四七),二二八事件爆發了。那年我剛三歲,父親二十八歲不到,當時任職基隆港務局總務科長。
那年二月二十七日,臺北發生了一個緝煙衝突事件,政府緝煙人員因故打傷了一臺灣人煙販,又打死一個路人。次日,臺灣各地群眾發起暴動,焚燒了煙酒公賣局又攻占了警察局,憤怒的臺灣民眾與政府軍警對峙,事態蔓延,很快就演變成臺灣人攻擊「外省人」的局面了。因此,大陸人都不敢出門,也有四處逃難的(據一九四七年三月一日美國駐臺大使館信函文件記載,當時有不少大陸人逃到美領事館避難)。其實,在二二八事件之前,人們就已經預感到「大災難隨時會爆發」,因為「早在一九四六年末,失望和不平已經在臺灣,尤其在城市中十分普遍,緊張的局面不斷升溫」[參見Lai Tse-Han, Ramon H. Myers, and Wei Wou,《一個悲劇性的開端:臺灣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的起義》(A Tragic Beginning: The Taiwan Uprising of February 28, 1947)(斯坦福大學出版社,一九九一),頁九四]。至於二二八事件的真相,當時美國的《紐約時報》(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九日)也有詳細的報導。
我父親身為大陸人,又是政府公務員,當時處境極其危險。因為有些臺灣人為了要出氣,只要看見外省人(不會說臺語的)就出手打殺。那時,我們家住在基隆大沙灣港務局宿舍,職員上班必須乘港局小渡輪。事變發生後,這裡的職員都不敢出去上班了,一因港內槍彈亂飛,二因渡輪上的工人全是臺灣人。只有我父親每天照常乘船上班,因他平素同情體恤屬下的臺灣員工,與他們交了朋友,這時就受了保護,來往平安無事。但到三月八日,不料國民黨軍增援部隊,由福建乘登陸艇蜂擁而至,一舉控制了基隆高雄兩大港及要塞。士兵一上岸立刻向臺灣民眾不分青紅皂白地開槍掃射。於是,忽然之間,局勢一變而成了外省人屠殺臺灣民眾的慘劇。軍隊遇到臺灣人,凡不會說普通話的,馬上就地處決,血染基隆港,遍地是血腥。
沒想到這麼一來,我家又緊張了,因我母親是臺灣人。她曾住過北京,故學會了「普通話」;可是,萬一有人聽出她的臺灣口音來,那怎麼辦?一時全家憂心忡忡,如坐針氈。
部隊登陸那天,槍林彈雨,父親被困在港務局的大樓裡,不能回家。傍晚,母親開始緊急應變。那時,我和大弟還小(小弟尚未出生),完全幫不上忙。母親一個人挪開榻榻米下面的墊板,彎著腰爬到水泥地上,清理地上的泥沙,然後把一床厚棉被鋪在地上。那些日子裡,只要一有槍聲,或巷子裡有嘈雜聲,母親就急忙掀開板子,帶著我和大弟鑽進地下去,日夜都如驚弓之鳥。
那時我才三歲,然而在往後成長的歲月中,那可怕的情景還時而在腦海裡浮現。
【春到耶魯萬事新,選出校長人稱奇】
去年(一九九二年)春天,耶魯大學問題重重,人人怨言不絕。由於校長及副校長大失「民心」,二人先後辭職,一時耶魯頓失往年的氣派,內外諸事頗為拮据。幸而不久聘得一位慈祥和藹的老教授拉麻(Howard Lamar)為臨時「代理校長」,才能平靜地度過這一年。
轉眼間,今年春天已到。耶魯校園仍是出奇的美麗,到處賞心悅目,香氣襲人。唯一美中不足的是,經過這麼幾個月,新校長仍遲遲未能選出,使人無限氣餒,以為校董會諸人意見分歧,無能行事。突然間,四月十五日早上十一時,我接到校長室祕書的電話,說校董會已選出耶魯同事雷文(Richard Levin)為新校長,將於五個小時後正式公佈,請我於當天下午四時去參加宣佈大會,但在那以前請我暫時保密。
掛了電話,心中有說不出的驚喜。喜的是,平易近人的朋友Rick(雷文小名,我們一向如此稱呼他)一定可以帶給耶魯無限的希望,也能化解上一任校長所遺下的不良氣氛。
但頗令人深思的是,為何數月以來,居然沒有人想到雷文是個最佳人選?原來他早就被「選校長委員會」提名,但大多數人以為他不可能被選中。原因之一是,雷文雖具有領導才能,但他在行政經驗方面遠遠不及其他諸位被考慮的人選。其實,他被提名後不久就有人說,他絕不可能成為最後人選,因為他目前的職位只是研究院院長,在行政上即是副校長若燈的下屬,學校怎麼可能讓他跳到若燈的頭上,而將主屬地位顛倒?(按:若燈已被聘為賓夕凡尼亞大學校長,即美國常春藤大學第一位女校長,此為後話。)基於這種考慮,數月以來沒有人討論到雷文。一直到四月一日左右才終於有人(包括他自己)考慮到他或可成為新校長的可能性。
其實大家所以沒想到雷文會真的被選中,最主要的原因乃是他自己本無做校長的野心──相較之下,許多被考慮的人選均公然地野心勃勃,他們的響亮名字常在報章上出現,亂人耳目。反之,雷文只安心做他任內的事。直到最近發現自己居然被鄭重考慮時,才真正想到當校長之事。這種虛懷若谷的精神使我想到老子《道德經》所說的:「虛而不屈,動而愈出。多言數窮,不如守中。」(第五章)──意思是說,廓然空虛者能包容萬物而生生不已,但多所設施者反招致敗亡,所以不如抱守清虛,無為無欲。
最有趣的是,雖然這次大家都沒想到雷文會成為新任校長,但還在十多年前(當雷文還是三十歲出頭的助理教授時),已故校長嘉馬地就預言道:「有一天雷文會成為耶魯校長。」這個預言大家早已忘了,現在突然又想起來。例如耶魯資深董事路克先生最近想起此事而歎道:「嘉馬地並非什麼算命先生,能預卜先知。但他有過人的智慧,才能看出天才之潛力來。」這使我想起,數月前自己隨口說出的一句話竟也實現了,可謂巧合──我說,希望耶魯大學「選出一位像嘉馬地那樣為理想而奉獻生命」的新校長(見,〈永恆的座椅:是選校長還是選總統〉,《聯合報》副刊,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)。果然,現在雷文被選為校長,全校師生紛紛把他比成嘉馬地──當年嘉馬地也是從未料到自己會當校長,而被選中時也是一樣謙虛。嘉馬地當時既年輕又缺乏行政經驗(比雷文更少行政經驗),他從未當過系主任或院長,僅只當過「人文學科的主席」。但多年後的今天大家一致公認嘉馬地是「校長中之英雄」,仍對他的所作所為牢記在心,時時引為佳話。就如耶魯社會學教授耶利克森所說:「做校長成功與否不在於一個人有多老、多有經驗,而是看他有多少智慧。」
其實這種所謂的「智慧」與老子「虛而不屈」的思想暗暗吻合。這又令我想起另外一件與選新校長息息相關的事來。原來今年若非代理校長拉麻以犧牲小我的精神來挽救學校危機(他以七十一歲高齡每日工作到深夜),則耶魯也不可能如此順利地度過難關。由於拉麻為人謙虛和氣,才漸漸把上任校長所遺下的敵視氣氛轉為團結與希望,功勞確實不淺。憶及去年拉麻教授被選為代理校長時,他也是驚奇不已──因為他自己早已準備於六月底退休(滿七十歲),萬萬沒有想到大家突然請他擔任如此要職。經過考慮之後,甚得人緣的他終於答應做一年臨時代校長。消息傳出,果然全校一片喜氣洋洋。有趣的是,就因為他最沒有野心當校長,大家才更加信任、尊重他。
於是,前幾天(四月十五日當天)宣佈新校長雷文的同時,我們又為另一件意外消息驚喜不已──原來耶魯校董會全體投票通過,將拉麻的職稱由「代理校長」改為「第二十一任校長」(而雷文則將於今年七月一日以後正式成為第二十二任校長)。這突來的消息使在場人士忍不住落淚,都頻頻向滿頭白髮的拉麻致敬。最後校董事路克先生轉頭向拉麻說道:「您是我們的英雄,我們對您的感激無法用言語來表達。」接著全體師生掌聲如雷,在一片歡呼中逐漸散去。
沒想到耶魯大學原來想找一位新校長,現在卻得到兩位校長。此乃史無前例之舉,特記在此,以供讀者深思。